普尚吉總是說:我當上瑜伽老師,是源於一個「錯誤」設定,一個預設讓我成為了瑜伽老師。
但我們可以這麼說: 世界上的確少了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,卻誕生了一位傑出的「瑜伽學家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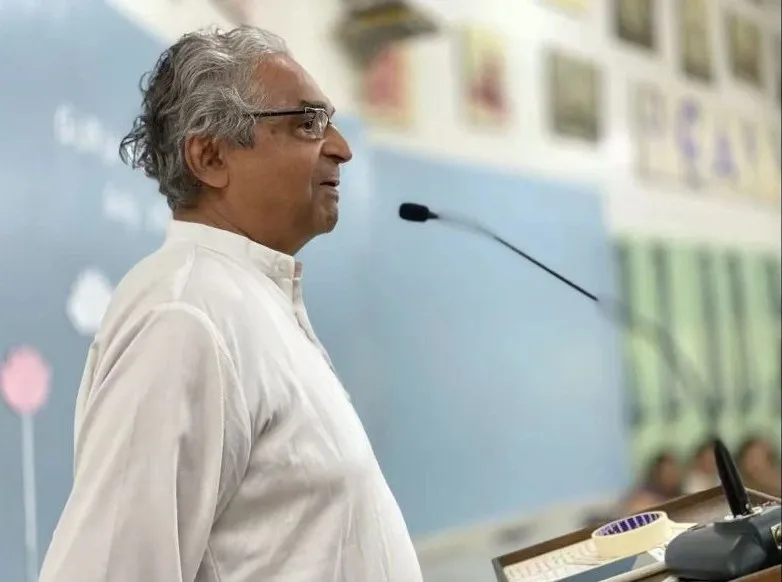
承襲瑜伽的傳統——總有那樣的時刻,你會面臨抉擇,糾結於如何做出決定;在這座「迷宮」的某個角落,你會發現那個更具創意的選擇,而它將對你有所助益。
大約是在1969年到1970年之間,我開始了瑜伽的練習。不用說,我的身體非常僵硬,完全無法適應瑜伽的嚴苛要求,但我仍然刻苦練習,每天都不間斷。一天下來,我全身酸痛,但我依然會繼續努力。
在1969年到1970年之間,我以「學徒」的身份開始教授瑜伽。那時我還沒從大學畢業,大學課程安排在早上,而晚上則空閒下來,所以我開始教朋友瑜伽。後來,一位艾揚格大師學生的親戚也加入了我的課程。我總共只教了三、四個學生,每節課賺5個盧比。
1972年下半年,我大學畢業後,V.Y. Patil先生希望在Pimpri開設瑜伽課。不管學院有什麼活動,他都會來參加,直到今天,他仍然來上課。艾揚格大師同意了這個請求。HAL在Pimpri有一家抗生素藥廠,工廠對面是HAL娛樂中心,這個設施是為員工及其家屬設立的,瑜伽課就在這裡的禮堂舉行。
Geeta 和我開始每週五去 Pimpri 上課,公司付給我們每人 250 盧比,Geeta 已經在其他地方開始上私人課程了。對我來說,這可是相當可觀的一筆收入!學生的數量也比家裡的多,但我不想漲他們的費用,仍然是每節課 5 盧比。
在1975年1月19日,拉瑪瑪尼艾揚格紀念瑜伽學院(RIMYI)正式成立,那年3月,我開始在學院上課,學院的學生數量穩定地增長,我要教很多課,因此我要求以前跟我的學生,從那時起,都來學院上課。他們同意了這個建議,但希望學費還是每節課5盧比,學院那時是25盧比一節課,我建議收20盧比。所以過了一段時間,他們也願意像其他人那樣,付25盧比一節課。

Geeta、Shah先生和我,除了艾揚格大師之外,還有幾位老師,包括大家熟悉的般度先生(Pandurang Rao),他在周日教授兒童瑜伽,也偶爾幫我們代課。從接待到上課,我和Geeta都需要分擔,還有負責收費的工作。她教課時,我負責收費並開出收據;而當我教課時,她也同樣負責這些事務。人們來付費上課,我們接受,這也符合艾揚格大師的原則。他曾告訴我們:「給予的應該比你們接受的多,不要追逐金錢。」
學生人數增加的同時,我還兼顧學院的財務工作,平衡收支成了我的責任。我會將總帳和分類帳交給特許會計師處理,我這樣做了十年。直到1985年,學院才聘請了一位正式的財務人員,每兩週來學院對一次帳。我的日常作息包括三個小時的瑜伽練習、教課,並開始每天閱讀五到五個小時的典籍。
有一天,我欣喜地發現,沿途走來,我的經濟問題已被妥善解決。
閱讀古籍——他開始認識到自己的潛能。隨著時間的推移,他找到自己與某種事物的聯繫,而正是那樣的事物引領他追隨自己的興趣。他逐漸找到自我,並透過探索將思想提升至瑜伽哲學的境界。
我內向的性格,更多地讓我趨向了哲學,潛質(Sanskara-s/Samskara-s),即與生俱來的行為方式,終於在我內心表現出來了,我感受到我內部的改變。1972年大學畢業之後,我轉向了哲學,因此閱讀和解讀古老的典籍,開始變成了「我」。我讀到的第一本書是Bai Gangadhar Tilak先生寫的「歌道」(Geeta Rahasya),這本書驅使我繼續去讀了奧義書和印度古典的六大哲學(Shat Darshanas)。
六大哲學的簡要概述,均收錄於《邀請您來讀典籍》第二冊(Invitation to Yog Texts – II),請大家務必仔細閱讀。
我幾乎每天都讀6到7小時的書,這為我開啟了新的信念。我讀了《Bharatiya Sanskruti》,它構成了印度哲學的基礎,而哲學也成為了我瑜伽研究的核心要素。
艾揚格大師的Guru(上師)克利希那瑪查亞(Krishnamacharya)於1962年來到浦那,我記得他對艾揚格大師說:「普尚傾向於哲學。」1979年,克利希那瑪查亞先生再次來到浦那,當時是艾揚格大師61歲生日。在這次訪問中,我們一起花了好幾個小時討論,他向我講解了一些「數論」(Sankhya),我們的討論內容都圍繞著這些學派的思想。當他離開浦那時,他對艾揚格大師說:「可以讓普尚繼續他的閱讀,但不要讓他讀《禿頂奧義書》(Mundaka Upanishad),那是指引人遁世的經典文集,他可能會變成苦行僧。」
我聽後大笑,說:我已經讀完了。
我早已開始背誦經文、學習詩頌,它們也被我唱誦出來──以我的觀點,這讓它們更容易被記住。
音樂,靈感之源泉 ——“1988年12月14日,艾揚格大師70歲;1989年3月,我出了那場車禍。”
那場車禍,從裡面徹底改變了我,那時的我已經開始了深入閱讀和研究奧義書,讀了《薄伽梵歌》(700頌的印度典籍版),也研究了Vinoba Bhave的各種解讀版本,加上印度語的其他解讀版本,每天都要讀至少6、7個小時書,哲學的各種解讀版本,加上印度語的其他解讀版本,每天都要讀至少6、7個小時書,哲學的各種解讀版本,已變成我生活的主流閱讀。
每天6、7小時的閱讀、3個小時的習練,讓我沒有太多時間練琴,那就是為何到了1977年,練琴的時間開始大幅減少,只在周日練琴,最後一次個人音樂會是在1979年舉辦的,那是為了慶祝我學習過的那所小提琴學校成立30週年——浦那的Uhydye的Violindan Vidyeala。
那次車禍之後,我的小提琴,永遠下架了,我失去了拉琴的能力。
他在講述這次不幸事故時,沒有絲毫怨言;對他而言,還有其他的路可走,無不充滿小提琴給他的激情和夢想。
我雖然收起了琴,但音樂在我的裡面還在,它一直影響著我的瑜珈教學、我的教學用語;音樂,讓我在詞窮時,可以去表達我自己,這也增加了表述上的微妙。
他充滿了積極的態度,他在自己的內部看到了「轉識成智」的能力,他堅信,他教學,不是為了讓人去崇拜他,而是希望能將瑜伽教育,給到他的學生,讓那些聽他課的人,可以真的學到東西。
在那次車禍之前,我早已開始閱讀和研究《薄伽梵歌》;車禍後,我打算開始解釋這些詩文,給那些想聽的人。早在1976年,我開始在學院的一些慶典活動上背誦梵歌,我這樣持續了18年,每一年,我都會背誦《薄伽梵歌》的一些章節,然後解釋這些詩文所揭示出來的哲理。

背誦的能力、對音樂的摯愛,在我的教學能力中,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,在我的發聲和用詞上,或許有一些天賦的東西,會自然流露出優雅和韻律,我開發出了即興講話的能力,是音樂激發和拓展了我的潛質。印度古典音樂擁有的無限廣闊的空間,讓我們能夠展現音樂屬性獨具的音階的語言風格。
到了今日,我上課是不備課的,我不會事先決定要講什麼,每堂課的唱誦之後,教學才開始「流淌」而出。
車禍前,我已開始給一個學習小組教《瑜伽經》,但因為那年3月的車禍,一年多都無法回去工作,因為我不在,《瑜伽經》的教學也就停了;到了2018年,它又重新開始,每個週日的早上,課程由我的外甥Shrineet和我,一起舉辦。這次重開,又受到新冠疫情的隔斷,後來在線上繼續開課,直到195節經文全部完成講解。
感謝普尚吉如此坦誠的分享,Namaskar!
本平台已獲原作者授權在海外設立網站,歡迎與原作者確認!
未經授權,不得轉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