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詞(吳會詞女士),就即將發布的《三角式之歌》 (Alpha and Omega of Trikonasana),
對譯者梁洪進行了「隔空」訪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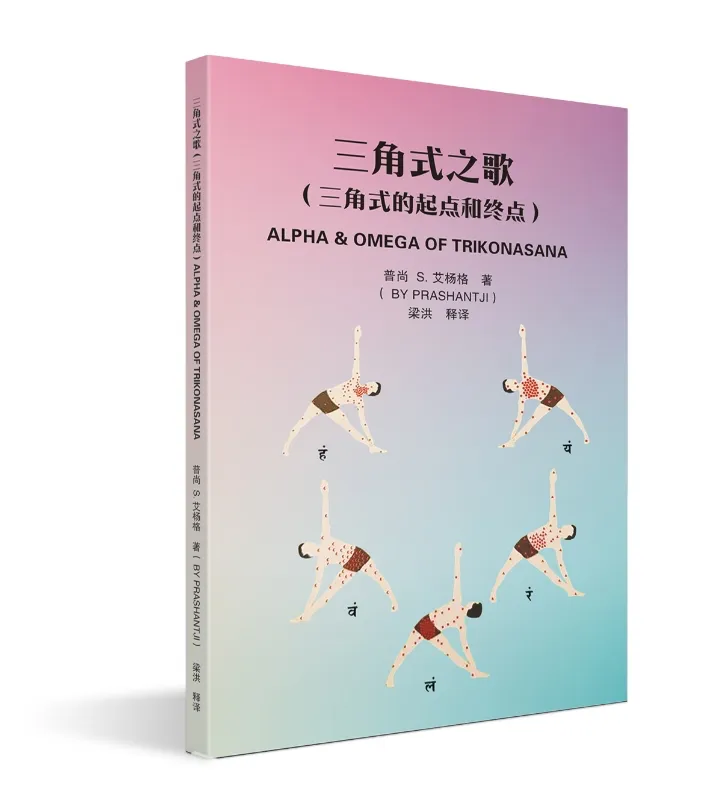
阿詞:普尚吉的書很多,僅在中國大陸,您已經給了我們八本中文譯作(《呼吸之歌》被分為了上+下),如果加上即將發布的《三角式之歌》,就有九本中文譯作了;在這些書裡,就您個人的感受而言,哪本最難?是《三角式之歌》嗎?據傳聞,您翻了12年。
梁洪:普尚吉的瑜伽教育,在中國大陸,是順應著艾揚格瑜伽體系的蓬勃發展而起,因此要感謝為普尚吉教育架設高架橋的所有中外老師們;普尚吉是一個高產的作家,已經被翻譯成中文的書,只是其中的一部分,當然也是最基礎的“教材”,全都是普吉在他的課堂上。如果您沒有涉獵過他的其他書,《三角式》就是最難的;如果經過了多年的課堂教育、其他書籍的滋養,《三角式》算是最易。這個道理,適用於他所有的單本。
或許應該這麼表達,最為重要的不是這本書最難還是最易,這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,因為無論難易,我們都要學習、理解;應該這麼想:學習一個三角式,不一定最難,我們不是都學過了、還能做嗎?但從三角式裡,學到瑜珈的真諦、精髓,應該很難,甚至最難,因為它被人認為只是一個基礎站姿,因此錯過了這班透過它學習瑜珈的「車」。
阿詞:將普尚吉的書譯為中文,您說過,絕不僅僅是“翻譯”,更重要的是“釋譯”,請教洪姐:何為“翻譯”?何為「釋譯」?它們如何關聯?如何不同?
梁洪:“翻譯”,很像普尚吉說的體式裡的“做”(Doing),而“釋譯”,就像對體式的閱讀、理解。我們既要“做”,要”譯”,但更要透過“做”或“釋”,去閱讀、理解這個體式和體式的教育。
阿詞:身為譯者,光是英文好就可以做到嗎?在您「創作」《三角式之歌》的過程中,如何考慮、權衡作者普尚吉與讀者/瑜珈修行者之間的關聯?作者—譯者—讀者,三者之間的平衡,隱含著怎樣一種「原理」?
梁洪:普尚吉與讀者/瑜伽修行者的關係,不是他關心的問題,他與瑜伽這門學科的關係,才是重點——口耳相傳的吠陀傳統,在普尚吉的「分享」中,表現為他教學的突出特色。他從不刻意培養自己的弟子,他總是說:要做瑜伽的學生,不要做我的學生或任何人的學生;我教的是瑜伽,所以你們該透過我、去學瑜伽。
阿詞:您常常在「導讀課」上說,有些詞,您幾年以後才懂,有些意,也總是可以懂得更深,只要您不間斷地學習,譯作就可以一直改下去,請問:您所說的「改」基於何「因」?為了何「果」?普尚吉的原作為何不改?作為讀者/瑜珈修行者,該如何理解您的「改」與普尚吉的「不改」之間的動態?
梁洪:是普尚吉教的「瑜珈」(Yog),太深廣了,怎麼可能很快就懂?我相信,普尚吉也不會很快就懂,他也是“翻譯”,比如說,他也要“釋譯”《瑜伽經》,他也要學習、研究,然後,再通過他自身在瑜伽體式這所瑜伽的靈性“學院”/“研究院”的畢業、當上了“教授”,再分享給我們。我透過「翻譯」的學習,幾年、十年、甚至幾十年,才能搞懂某個詞,那太正常了,不這樣,才不正常吧?因為普尚吉在透過他的課堂、他的每句話、書裡的每個闡述,講述《瑜伽經》或《薄伽梵歌》的概念,所以我有時以為懂了,但其實還不明白。所以,說到“改”,為何一本《三角式》的小冊子,要翻譯12年,那是在不斷地學習、研究、領悟,必然會導致不斷地改稿,總不能一直都停留在“不懂”吧?每次,都是改到下廠印刷的最後一刻,有的書,甚至下廠後也改過,不能去計算成本了,這份使命不允許我去計較,“自己抗”,是我的榮幸、是神的恩典。因為有時候理解錯了,自己不知道,可能就在下廠前的一天,上了普尚吉的的某節課,「剛巧」他講到了那個概念,也已經不是一次「剛巧」了。難道我裝沒聽見嗎?改!而普尚吉的原作,之所以無需改,是因為在理念上,已經是終極真理,他講的是無上智慧,他悟到了它們,我們沒有,我們認知到那些的,是階段性的知識、是相對真理。但原著裡的錯字、排序,甚至有時候圖表,都有錯誤,那是編輯的問題。不是普尚吉的問題,他的書,是說著“寫的”,因為他的手臂問題,在公眾號的前期推文裡,他自己已經講過了。我在中文版裡,能改的,都盡量改了,你們身為讀者,也貢獻了不少糾錯,在此統一表示感謝!請繼續你們的這個行為,每本書,其實都是我們的共同創作。
阿詞:您在《三角式之歌》裡多次提到要去關聯普尚吉的哪些課程,哪些書,那些課程您都是深度體驗過的,並且也透過平台給了我們,但那些書對我們卻很陌生,比如《廣林奧義書》,根本買不到中文版,《瑜伽經》雖然有什麼想讀本身為普尚吉的忠實的學生,身為古典瑜珈的虔誠的學生,您平常都讀哪些書?您是如何學習的?
梁洪:我自己也沒有這些書,都是從普尚吉多年的口耳相傳之中,學到了一些皮毛。我的學習方式,其實非常笨,就是重複,真的沒有其他的特別之處,沒有什麼秘密武器。我的重複,其實不是重複,而是在重複中有源源不絕的新感悟,即便是同一個說法、同一個詞,這次聽課懂了,但下次復盤時,又浮現出了不同的內涵或意義,茅塞頓開的感覺,那很有趣、很奇妙,所以學習不能讓自己感到枯燥、生味,不能把它弄出大餐,而是把它弄出大餐,而是慢慢吃所以,即便是皮毛,對於目前的我而言,已經消化不了,再加上要翻譯他的課和書,所以精力有限;偶爾得也會到的一些書,我會當作參考書,它們也的確做出了巨大貢獻,讓我從一枚純白的小白,到開始理解一些重要概念。普尚吉完全了解大家的這些困難,他隨時掌握著信息,因此他給了一本書:《邀請你來讀典籍》第一冊和第二冊(Invitation to Yog Texts-I,II),他了解他的學生的困難,得不到一些印度古老的文本,有些在印度也快失傳了,所以多年來,他自己學了、研究了、通悟。在我心裡,他已是古老典籍的傳承利器、神器,我可以“偷懶地”跟著他學,吃進去了不少瑜伽聖典“美餐”,因此,也需要好好消化。
阿詞:無論是普尚吉的課還是書,裡面都有大量的梵語,關於梵語這一塊,您是如何聽懂、如何看懂的?經典瑜珈的學習離不開梵語,《瑜珈經》、《薄伽梵歌》這類巨著,都是以梵語的形式傳承的,我們手裡的譯本也是天城體的拉丁轉寫,作為瑜珈的愛好者/修行者,我們該如何著手?面對大量的梵語,我們這些外行人該如何學習?該以何種心態來面對?
梁洪:我也開始抽空學習梵文了,從字母學起,很慢,因為翻譯、校對的任務非常繁重。一開始,不是為了學梵語而學梵語,而是因為普尚吉的調息課,要求我們準確地讀出梵語字母表,那是非常重要的“能量行為”,要在體式裡進行,所以逃不掉地要學,我為此也和許麗珍女士,共同出了《梵語輕鬆學》的字母、體式名等,為學的我暫時沒有找到其他目的要學梵語,因為學習、研究普尚吉教的瑜伽,已經很需要精力,加上“翻譯、導讀的Dharma”,即我的使命,就很難分出時間認真學習梵語了,那幾乎需要一個人集中全部精力去好好學習。在這麼多年的累積裡,也在不知不覺間,跟著普尚吉,也學了不少梵語,他每堂課,幾乎都在重複一些瑜伽術語的梵語形式,這樣的學習,毫不費力,所以得到它們時,也不會很興奮,更沒有雜念,反而能繼續學下去,因為不會吃“撐”。
阿詞:英譯者中對譯者的中文存在著極大的考驗,尤其是形而上的哲學領域,遣詞造句無不限定在譯者的中文表達之上,作為古典瑜伽的學生,您是如何理解英中轉換的?在翻譯《三角式之歌》的過程中,您又是如何憑藉良好的中文素養,承託了普尚吉借助英文傳承的這部巨著的?在這個過程中,您是否受到了一些人或書籍的影響?能舉例具體講講嗎?
梁洪:我的中文一般,英文比較一般,但它們顯然都不是障礙,這也是因為瑜珈的習練、普尚吉的教育,讓「言語行為」淨化、提升了我的中文,不是我的中文自己有什麼提升。讓我們完整起來的,是體式裡多年培養的智性、記憶力、想像力,它們都會得到深廣的開發,這個過程雖然看起來很慢,但很怕疊加效應,就像一萬塊錢,被存入了銀行,到期連本帶息地重新存進去,幾年後、幾十年後的複利,會是一個驚人的、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。例如「Sensitivity」這個普尚吉常用的詞,幾乎耗了我十幾年的時間,即使當面請教他,也不得其意。直到搞清楚了五個行動器官、五個認知器官,在體式裡的作用、行為、目的、功能,才發現,Sensitivity不是字典裡的什麼“敏感”“靈敏”,普尚吉在這個方面,用的是另外一個詞,即acute。 Sensitivity,指我們身心內在的“感官力”,即感知力、感覺力、感受力。眼睛,無法穿過骨肉之軀,看到內在世界裡的微妙存在,那是醫療儀器都無法掃描出來的存在,所以瑜伽培養了我們的感官,它們開始內收時,就會開啟內在的「視覺」、「聽覺」等等。所以我們做翻譯的,有責任和使命,把這些超越字典意思的意思,傳達給大家。否則,普尚吉的苦口婆心,就都白費了,這是我們的損失,不是他的損失。
阿詞:什麼樣的瑜珈學生適合學習普尚吉總院的會員課?英文不好的瑜珈學生,有沒有可能去上普尚吉的會員課?我們到底離普尚吉有多遠,能幫我們具體分析分析嗎?
梁洪:普尚吉的課,連英美國家的學生/老師,都很難懂,即使有幸進入總院的課堂,也是一知半解,這是絕大多數人的體會。英國的「睿叔」(Mr. Richard Agar Ward)曾跟我開過一個英式玩笑:洪,你最近完成了三角式的英文翻譯嗎?普尚吉的書或課,即“普尚吉語”,需要先翻譯成正常的英語,再翻譯成中文。所以這反而成了我們的優勢,全世界艾揚格瑜珈體系的學生,不分國界、種族、膚色、年齡、性別,在普尚吉的課堂上、書裡,都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,誰真的克服了困難,學進去了,誰就能掌握這門「瑜珈語」,它超越英語、法語、中文,所以不要一點氣,所以不要一點地累積。有什麼在催命嗎?說你一定要馬上懂?普尚吉在2025年6月4日的課上說;「你們都說我教的瑜伽很難,你們當初學頭倒立,不難嗎?你們在世俗的生活裡,不難嗎?你們為何還是學了、活了呢?覺得難,是你們沒有克服自己的習慣、慣性思維。你們多年跟著某老師
阿詞:作為譯者,在翻譯的漫長過程中,應該會與作者產生深度的“量子糾纏”,您的感受會演化成普尚吉的感受,會去觀察普尚吉的觀察 ,去學習普尚吉的學習,去理解普尚吉的理解,去研究普尚吉的研究,去實驗普尚吉的實驗,被教育是反常被教育……這個過程嗎?那麼,多年翻譯普尚吉的作品,您「變了」多少?能具體講講嗎?
梁洪:常常會發生這樣的奇妙之事,某個詞,怎麼都不懂了,也無處可查可了,當天晚上的「日常」習練中,如果是跟著普尚吉的課堂錄音,就會突然聽到答案!這已經發生了很多、很多次了。我只能說,Namaskar! 阿彌陀佛!另外關於「合體」的翻譯程度,我只能透露我的夢想:
如果普尚吉突然會說中文了,那麼他就是按照書裡的語氣、習慣說的;因此,那些不是我的翻譯,是他通過受過他教育的“我”,在用中文傳達瑜伽的奧義;當然,我離這個夢境,還差太遠、太遠。或者,換個說法,普尚吉拿到這些譯作時,突然想找個印度本地他信得過的翻譯,將它們翻幾句給他聽,那麼,我不允許自己的譯作裡,有任何錯誤的理解或說法。如果只是翻譯,《三角式之歌》在我拿到書的那年,已經完成;為何要等12年?在這本書裡,希望你們找到你們各自的答案。
阿詞:如果《三角式之歌》是您最後一部向世人呈現的普尚吉的譯作,而今年又是最後一年的傳承班的“導讀課”,那麼,從明年開始,您又將如何帶領我們這些中國的瑜伽學生繼續前行?中國的瑜珈學生,多數是不能獨立聽懂原版的「普尚英文」課程的,尤其裡面還包含大量的梵語,我們又該何去何從?
梁洪:原本打算它的確是收官之作,我也馬上奔6了,想再次退休,專心學習他的課、書,那是我最幸福的晚年生活了;但普尚吉以77歲的年齡,還在寫書、出書、講課,我沒有理由躺平去學習,可以將繼續的翻譯,當成學習的一部分。明年的分享方式,還沒計劃好,但基本上還是以他的課為主,讓他說、讓他教、讓他的話語去導讀他的話語,一直都是我導讀的原則。我自己沒有資格開自己的“課”,因此能導讀他、翻譯他,已經是超出我對自己的預估了,因為即使普尚吉同意讓我自己開課去講他教的瑜伽(他的仁厚,讓他同意了不少追隨他多年的人,自己開課去教他的東西),我不認為我講的比他高明,那為何不讓這位瑜伽士自己去講,我盡自己所能地提供給有興趣的同學一個共享的平台,我們只負責去理解、再去分享我們的理解呢?就算我們說錯了,那也是我們做學生的權利、特權,但如果我們是老師,那份“責任”,至少我自己,擔不起啊。
Namaskar!
本平台已獲原作者授權在海外設立網站,歡迎與原作者確認!
未經授權,不得轉載。
